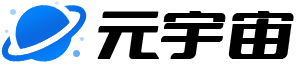辛顿的冬与春
一个试图破解万物奥秘的人,却因自己的求索背负了沉重的十字架,直到坟墓中也没卸下。
这是宇宙残酷的小玩笑。
正是在1947年的冬季,伦敦西南的温布尔顿,一个叫做杰弗里·辛顿的小男孩呱呱坠地。
站在辛顿和爱因斯坦的切近,你找不到他们的任何共同点,除了两人都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。
相隔102年。
但如果退到崖边远眺,你也许会惊奇地目睹:历史的齿轮旋过几代人头顶,经过102年的漫长行进,正再次严丝合缝地啮合在一起。就在那齿轮弹撞的一瞬间,两人靠得很近。
历史的交接,沉默的巨响。
人们抬起头,一切如常。

GeoffreyHinton
最近十年,不特别冷的日子,辛顿都会住在自己的岛上。
没错,是他的岛,一个点缀在加拿大休伦湖畔,完美符合人们对“人工智能教父”名头浪漫想象的岛屿。
他在65岁时买下这座岛。而在65岁以前的任何一天,他恐怕都没幻想自己能这么奢侈地“消费”。
在那之前30年,辛顿只有一个身份:计算机科学教授。
现在人们很自然地把他做的事情称为“人工智能”。但时钟拨回上世纪70年代,这不过是一个只有幻想家和疯子才愿意投身的冷门学科。
甚至研究者本人都觉得“人工智能”这样的词太过艳俗难以说出口,一般称自己搞的是“机器学习”。
而辛顿所投身的,又是机器学习里冷门的一派:神经网络。
简单来说,就是用计算机模拟人类大脑的亿万神经元连接,从而涌现出“智能”。
可具体怎么“涌”?真是鬼知道。
在打长途电话还要人工接线,电脑刚刚开始小型化,出门只能靠纸质地图的Lo-Fi年代,人造神经元之类的话听上去就像梦呓。

1970年生产的IBMSystem3电脑。

GeorgeBoole
1815-1864
布尔妻子的叔叔是地理学家,他的姓氏Everest命名了珠峰;

EthelLilianVoynich
1864-1960
辛顿的曾祖父查尔斯·霍华德·辛顿是数学家兼奇幻作家,发明了“四维立方体”,就是你在《星际穿越》里看到的四维空间;

8岁的辛顿在动物园里和蟒蛇合影。
他懵懂地意识到:生命对环境的反应模式并非完全随机,而是遵循某种“直觉”。
这种直觉既不像数学公式那样简单输出,也不像宗教宣扬的“灵魂”那样不可琢磨。
它有迹可循。
就在小辛顿蹲在爬满冷血动物的大坑旁边的50年代,大洋彼岸的美国心理学家弗兰克·罗森布拉特行动了。
他改造了一台硕大的IBM计算机,模拟出几百个神经元,想让它从识别字母和形状开始,最终成为一个生命。
这就是后来一切“神经网络”的母机——感知机。

BernardWilliams
威廉姆斯是一位道德哲学家,他一生都在跟一个敌人战斗,那就是——还原论。
“还原论”,其实是当时主流科学的一个假设推论:
万事万物,无论多复杂,都可以拆解成一个个边界分明的、有特定功能的“零件”。
这意味着,想要复刻某个系统——包括人和动物——只需找齐所有的零件!

BladeRunner(1982)
给机器强行输入概念和规则,被归为人工智能的“符号主义”流派,它扎根于“还原论”;
而用人造神经系统整体模仿人的学习过程,就归为“神经网络”流派,它源自于“系统论”。
而后几十年,两派势同水火,各不相让,表面上是技术路线之争,实际上却是对世界本质的“押注”。
赌的就是:这个世界究竟是一堆利落的“零件”,还是一坨牵一发动全身的“浓汤”?
这里,我们不妨明晰一下“符号主义”和“神经网络”在方法论上的根本区别:
在“符号主义”的方案里,最小的零件就是“概念”。
例如:食物、酱汁、调味品、甜、味道、红色、番茄、美国、炸薯条、蛋黄酱、芥末,这些都是概念。
所有概念用规则相连,组成一个巨大的渔网。
而新概念,例如“番茄酱”,则可以挂在刚才这些旧概念网眼中的适当位置,成为新的绳结。
新概念无穷无尽,渔网上的网眼也无穷无尽;
旧规则不够精准,也需要用无穷无尽的新规则来完善。
例如:鸟会飞,企鹅是鸟,但企鹅是不会飞的鸟。

“神经网络”比“符号主义”更接近我们大脑的工作方式。
不过没人规定智能必须以类脑的方式实现,你完全可以“抄近路”。
而且造物主绝对是个“反鸡汤者”,因为很多情况下抄近路就是有效的。
1970年代,“符号主义”已经突飞猛进,能做出一些像模像样的推理,可是“神经网络”还停留在智障阶段。
这是一种极强的反馈。很多神经网络学者含恨倒戈,加入了“还原论”的阵营。
但辛顿无法说服自己。和小时候一样,他不能接受有什么东西违背了自己对世界构建的认知模型。
1972年,他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博士,方向就是“神经网络”。
如果别人无法找出原因,他就得自己找出原因。
如无意外,这次找到答案,要比搞懂公交车上硬币爬坡花费更长的时间。
就在博士的第一年,辛顿看到了一个其他人工智能小组做的实验:
一台计算机,连着两个摄像头,系统要自主控制机械臂把积木搭成汽车的形状。
这对于当时的技术来说是地狱难度。因为系统视觉只能靠轮廓识别散落的积木块,一旦堆在一起,它就不认识了。
让辛顿难忘的瞬间出现了:机械臂退后了一点,然后“砰”地一拳把积木堆打散。
如果有人这么干,你会觉得他是因为“做不到”而沮丧。在机器人挥拳猛击积木时,我感到了它有同样的情绪。
辛顿说。
拥有感觉,就是你开始渴望得不到的东西。

LudwigEduard Boltzmann
然而,玻尔兹曼当时遭到了一众科学家的激烈反对,甚至对异教徒似的攻击。
一个重要的理由是:你竟然用“统计数字”、“计算概率”的模糊方法来解释具有确定性的物理世界,这算什么科学?
反对派科学家的愤怒,本质上只有三个字:不承认。
不承认这个宇宙的复杂性超越人类的计算能力;不承认人类拼尽全力也只能以模糊的方式把握这个世界。
但宇宙不会因渺小人类的愤怒而改换它的基本结构。
放弃对“精确”的执念,正是撕开迷雾,找到那座连接“宏观”和“微观”之桥的重要前提。
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。
假如,你把各种颜色的墨水混在一起。
它们肯定会经历一个混合的动态过程,最终会完全均匀。(此时每个分子在各种可能状态上的概率是相同的。)

要理解霍普菲尔德的洞见,首先要知道“最小化自由能原理”。
无论在什么物理结构中,系统总会尽可能对外做功——就像小球总会往低处滚那样。
滚到相对低位后,系统就达到了“最小化自由能状态”,从而实现稳定。

这张图上方显示了一个“自旋玻璃”,它内部的无序性构成了一种稳态,产生了下方所示的复杂的“能量地形”。
霍普菲尔德的神来之笔是:
他没有用现实世界的原子制造“自旋玻璃”,而是用计算机的0和1不同的电位来替代原子状态,在赛博空间模拟出了“自旋玻璃”。
它也被后来人称为“霍普菲尔德网络”。

与地球不同,霍普菲尔德网络中山脉的最终走向不是大自然创造的,而是人设定的。
设定的方法就是“训练”。
例如,我们用“26个字母的形状”进行训练,最终这个霍普菲尔德网络的“地貌”就会被塑造成特定的样子,并且稳定在这个样子。(因为这个样子它的自由能就是最低的。)
此时,训练完成。

同时从很多个点向下扔小球,他们最终会停留到不同的位置。
比如我们站在这片山脉的上空,按照这样的排列方式扔一些小球:

生物神经元之间信号的强弱,和神经网络节点之间强弱的类比。
在相继登上玻尔兹曼和霍普菲尔德这两个巨人的肩膀之后,镜头从辛顿的脑后缓缓升起,鼓点声由远及近,他面前迷雾散尽,浮现出一座雄伟的大桥。
辛顿瘦削的手臂,接过了人类探索的熊熊火炬。
(四)蛹、汤、蝶
记忆并非智能的终结,它需要理解这些信息,最终用表达给予回应。
有心理学背景的辛顿很快就发现了要害:
也许是为了简便,也许是没有走那么远,总之,霍普菲尔德假设了存储的各项信息之间是完全独立的。
也就是说:霍普菲尔德网络在学字母表时,默认A是A、B是B、C是C。如果输入一个信息,系统或者判定它是A,或者判定它是B,不会判定它介于A和B之间。
这有点儿像硬币分类机,任何硬币都必然会落在某个预定的沟槽内:

这张图展示了词语之间语义关联的程度,颜色越红表示语义关联越大。例如“名字”和“性别”的内在关联就很大。
由此,概念之间不再是孤岛,而是依靠概率建立起了精妙的数学关系,形成了一个“语义空间”:
每个词在语义空间中都有一个坐标。
语义空间不是普通的三维,而是多维空间,也许有几百个,几千个维度。

这张图展示了用50个维度来描绘左边的词。每一个维度上的颜色都可以看作一个“亚概念”的强度。
有了这个“语义空间”,系统得以把概念拆碎,为每一个亚概念的“粉末”找到它的坐标。
举例来说:
普通的“通”和畅通的“通”,就包含某种共同的深层语义,我们能体会其中的亚概念,但却很难描述。
而利用亚概念进行学习,就相当于进入了“盗梦空间”的更深层,一瞬间打通了任督二脉,理解就产生了。
而且,它还可以在深层空间重新整合这些亚概念,吐出和学习资料不同的全新语句,也就是表达。
这正是辛顿要做的。
1983年,辛顿和他的合作者特伦斯·谢诺夫斯基宣布了这个新系统——“玻尔兹曼机”。

玻尔兹曼机:上面是可见层,下面是隐藏层。
玻尔兹曼机的训练,大部分工作其实就是对各种概率的计算,把计算好的参数固定在各个神经元的连接参数里,让这些神经元最终所构成的“地貌”能够逼近训练素材中所隐含的“地貌”。
这时神经元数量已经非常大,每一个神经元在“地貌”中具体起什么作用已经很难说清。
也就是说,人类没有办法对具体的神经元进行直接干预,只能使用某种算法来操作。
辛顿脑海里出现了“反向传播算法”。
你也许读过卡夫卡的《城堡》。
土地测量员K受雇于一个城堡,但当他来到城堡所在的村庄,却无法与真正的权力机构取得联系,但是他又确确实实地被那个高高在上的权力所影响和阻挠。

一个毛毛虫,就是训练神经网络的数据。它会变成蛹,而在蛹里,原来的毛毛虫融化成了汤,从这个汤中最终幻化出一只蝴蝶。
那么,从毛毛虫到蝴蝶到底发生了什么?蝴蝶和之前的毛毛虫还是同一只昆虫吗?
这些答案,如庄周梦蝶一般深刻而浪漫。
1980年代,接连祭出玻尔兹曼机和反向传播算法后,辛顿引起了小圈子的注意,但很快波澜就平息了。
不过他寻找真相的努力,为“神经网络”一派结结实实扳回一局。

辛顿在1990
(五)冬
虽然玻尔兹曼机所暗示的基于“系统论”的神经网络看上去很有王者之气,但要造出一个“能平视人类的AI”,则需要人类的计算力大幅增长。
不是一千倍,不是一万倍,不是十万倍,是十亿倍。
90年代,全球计算机的算力虽然已经起飞。但对于神经网络所需来说,仍如烛火之于太阳。
正如当年爱因斯坦高擎相对论,却因无法验证导致获得诺奖的日子一拖再拖那样尴尬。
辛顿改良了玻尔兹曼机,减少了神经元之间的连接,成为“受限玻尔兹曼机”,以此大大降低了计算量;他还设计了“模型蒸馏法”,可以把大模型中的知识转移到小模型中。
即便如此,所需的计算力还是远超想象。
“渴望而得不到”,这个孩提时代的梦魇突然又回来了。
或者说,它从未远走。
罗莎琳德患有不孕症,他们没办法生下小孩,最终决定收养两个南美洲的孩子。
就在一双儿女刚进家门时,罗莎琳德被确诊了卵巢癌。
治疗不孕症梦魇般的体验,让罗莎琳德对医生的冷漠和无能产生了极强的厌恶。
她拒绝手术和化疗,执拗地在家自己用一种非常冷门的“顺势疗法”,也就是把药物稀释到几乎无法检测的程度,然后输入体内。
“冷门”只是一种客气的说法——这种疗法是无效的。
罗莎琳德的病程发展很快,肿瘤越来越多,精神也越来越崩溃。她固执地相信自己肯定能好,开始寻找更贵的“顺势疗法药物”。直到她流着泪对辛顿说:“我们把房子卖掉吧。”
辛顿看着妻子,看着这个支持自己走过春天的眷侣,说出了此生最残忍的话:“我们不卖房子。如果你死了,我得照顾孩子们,他们要有地方住。”
哪怕30年已经过去,每每回想起这个瞬间,辛顿的心中还是会被各种情绪充满,那是愤怒、内疚、伤心、困惑。
那是一个智能生命面对这个世界的荒谬所迸发出的剧烈反应,那是一种辛顿尚且无法理解的东西。
辛顿站在了一生中自我怀疑的顶峰。
几十年对世界的观察最终都不可避免地滑向残忍的“自我剖析”:
如果人终归只是机器,那么这种滴血的情感,究竟藏在神经网络多么幽深的地方?
如果机器终究能成人,那么制造出一个AI让它终究尝遍人间苦难,意义又是什么?
妻子离开那年,辛顿46岁。他的儿子5岁,女儿3岁。

互联网的蓬勃发展,让全世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算力饥渴。
商业是宇宙中最猛的春药。摩尔定律开足马力,不仅用于科学计算的CPU算力打着滚往上翻,用于图形计算的GPU计算力也在蓬勃发展。
如果用1985年最先进的计算机运行一个计算,不停不息直到此时此刻。换做当下最好的计算机来做同样多的计算,只需要1秒。
最好的预言家也没敢想象:几十年的时光呼啸,算力的烛火真的变成了耀眼的太阳。
离离原上草,只待星星火。
一位出生于北京的女性引燃了火焰。
斯坦福大学教授李飞飞,带领团队用了800个日夜,手工标注了1400万张图片,分成了2万个类别,在2010年创立了ImageNet图像识别挑战赛,鼓励全世界研究者用AI分类出更多的图片。

奖品是——荣誉。
2012年冬天,当年的奖项揭晓,冠军归属于一个叫做AlexNet的系统。
它对图片识别的错误率低到了15.3%,比第二名的错误率彪悍地低了10.8个百分点。

以当时巨头公司手握的计算力,已经足够用神经网络做出实用的AI了!
来自世界各地的收购邀约如雪片般袭来:你们公司报价多少钱?我买!
师徒三人这才意识到——自己应该成立一家公司。
2012年末,草草成立的DNNresearch公司面对四个终极买家:谷歌、微软、DeepMind、百度。
他们决定搞一次拍卖。
瘦骨嶙峋的辛顿躺在出租车后座上前往拍卖地点。他19岁的时候帮妈妈搬暖气伤到了脊椎,几十年病情逐渐恶化,此时他已经没办法坐下,只能站立或躺着。
DeepMind是创业公司,只能用自己手里的股份报价,很快退出了竞争,微软出到2200万美元,也退出竞争。只有谷歌和百度不停地加价,从清晨到午夜,报价还在陡峭攀升,仿佛如果不买到辛顿三人,就要面对世界末日一般。
由于是远程拍卖,辛顿是在酒店里躺在床上和两位学生商量。
第二天早晨,新一轮报价争夺继续,谷歌已经出到了4400万美元。辛顿决定叫停拍卖,65岁的年纪和脆弱的脊椎实在没办法支持他到地球另一端的cn工作。
他决定把公司卖给谷歌。
谷歌花4400万买到的,像是个“空壳”,只有辛顿三人手中的知识产权和他们未来几年在谷歌工作的承诺。
但正如达尔文、哥白尼、加缪、爱因斯坦一样,三人手中所握的,不仅仅是知识产权,更是某种真相。
真相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尊严的东西,它重若千钧,也理应价值千金。
辛顿建议三人平分股份,各拿33%。两位学生不肯,执意让辛顿收下40%。

休伦湖的乔治亚湾
(七)圆环
杰奎琳对辛顿说:
“我感到很难过。但我知道,必须用剩下的时间好好享受生活,也尽量把你和其他人的一切安排好。”
他们在岛上散步时,偶然发现了一只小船的残骸。杰奎琳找来一些女工,把船整饬一新,成了一只酒红色的独木舟。
“她进行了首航,”辛顿回忆,“然后,就再也没人用过它。”
2017年,已行至生命尾声的杰奎琳见证了辛顿获得了计算机界的最高奖项:图灵奖。
名望大振的辛顿,试图用自己刚拥有的一切从死神手里抢人。
在加拿大政府的支持下,他火速成立了“向量研究所”(VectorInstitute),聚集了全世界顶尖的人工智能人才,第一个项目就是:把AI用于医疗诊断。
但几个月后,杰奎琳离开了世界。
辛顿想起多年以前,那个无法分辨积木的机器人。狂怒的一拳,崩塌的渴望。
他小心翼翼地把照片存在电脑上。
其中一张是他和杰奎琳的婚礼,在邻居家的客厅里交换誓言。那天辛顿荣光焕发,杰奎琳双手握住他的一只手。
还有一张照片,杰奎琳在酒红色的独木舟上凝望着镜头,水面斑驳,微风拂过。

IlyaSutskever&SamAltman
从这里开始,辛顿的人生才与大多数人了解的追光下的戏剧串接在一起。
在OpenAI,苏茨克维尔把玻尔兹曼机发挥到了极致,成为了深度神经网络“大模型”,大模型成为了ChatGPT的基础,也成为了如今一切拥有对话和理解能力的AI的魂灵。
人类第一次制造出能通过图灵测试的AI。
一万年来,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,从未如此模糊。

1973年,约翰·迪恩接受调查委员会质证。
从ChatGPT开始,人工智能研究突飞猛进,但研究者一直避免使用一些看上去不科学的词汇,例如“直觉”。
他们试着用各种理论拆解这种整体的直觉,例如“推理”、“计划”、“注意力”之类。但辛顿在很多场合都在高呼:“AI比我们承认的更具有直觉性。”
一旦试图把直觉拆解成细碎的零件,就会走上“还原论”的近路。
符号主义总说我们的本质是推理机器,那完全是胡说八道。我们本质是类比机器。
可能在上面加一点点推理,以便在类比出错误答案的时候注意到并且纠正它们。
辛顿说。
承认自己是直觉机器,代价是高昂的。
这意味着你必须接受自以为对世界的理解本质上只是概率预测;
意味着你必须承认自以为坚实的记忆本质上只是拼凑出的幻觉;
意味着你必须全然放下自己的傲慢,在荒谬的世界里前行,然后接受命运给你的一切。
不是每个人都付得起这个代价。
起初,人只是想了解这个世界;
为了了解世界,我们不得不了解自己;
而为了了解自己,我们创造了另一个自己;
我们创造出另一个自己,证明了我们永远无法了解这个世界。
辛顿一生所做的事情,就是站在这个荒谬的圆环中,指给世人看。

1963年,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的卡斯特罗和赫鲁晓夫。
2023年,伊利亚·苏茨克维尔认为OpenAI的CEO山姆·奥特曼漠视人工智能的安全建设,掀起了一场宫斗。
失败后,他离开了亲手创建的OpenAI,建立了安全超级智能公司(SafeSuperintelligence)。
辛顿公开表达了对弟子的赞许,但他却不确定苏茨克维尔是否能成功。
做出原子弹只需要让它爆炸,但确保某个东西不爆炸,要难得多。
辛顿说。
2023年,辛顿从谷歌辞职,是三人组中最晚的一个,他给出的辞职理由是:这样可以更中立地批评人工智能的危险。
如核威慑纪元一样,新纪元恐怕也会建立在新的威慑平衡之上。
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辛顿那个奇怪的比喻:把AI视为肿瘤。
如果所有的肿瘤都能切除了事,辛顿的人生为何还要承担那么多悲伤?
与其徒劳幻想切除,不如研究一种更积极的、与之共存的策略。
但这种策略是什么?
“没有人知道答案。”
辛顿叹息。

但这似乎并不是事实。
辛顿的人生所承受的荒谬,和你我一样。而世界上的绝大多数普通人,只能在岁月里前行,承担命运所给予的一切。
没有奖赏。
没有奖赏,直到他们撑到对岸,或没能撑到对岸。
一个诺贝尔奖,挂在辛顿的家族树上,似乎够格,甚至过于够格。
我常常想,我喜欢木工活,去做一名建筑师会不会更快乐?因为我不必强迫自己去做什么。
然而,对于科学,我不得不一直强迫自己,而且因为家族的原因,我必须在科学上取得成功。这些年的科学研究其中当然有快乐,但主要是焦虑。
现在我成功了,这是一种巨大的解脱。
辛顿说。

“我觉得他是那种随时需要人陪的人。”罗斯玛丽温柔地说。
罗斯玛丽给这位“木工老男友”辛顿定了规矩:一个人在岛上时绝对不许砍树,以防把自己胳膊砍掉了没人救他。
在纽约客记者罗斯曼的记录中,有那么一幕:
那天辛顿驾船上岸,等待罗斯玛丽给岛上带来补给。
他去商店里买了个灯泡,出来时,却一闪身扎进了商店门口的绿植中,很快他站起来,手里举着一条黑黄相间的蛇。
它扭动着身子,大概有一米长。
“给你的礼物!”他豪爽地举到罗斯玛丽面前,“我在灌木丛里发现的。”
罗斯玛丽笑了。
他把蛇从左手倒到右手,两只手都黏糊糊的。让罗斯玛丽闻一闻,充满了一种奇特的矿物味道,那是这种蛇所特有的。
“你的衬衫都脏了。”罗斯玛丽说。
“因为我必须抓住它。”辛顿解释。
随后,辛顿把蛇放下,满意地看它钻回草丛。
“今天天气真好,让我们远航吧!”他说。
辛顿又恋爱了。
此时此刻,在岛上的小屋里,那个酒红色的独木舟被透过窗棂撒下的阳光照耀得闪闪发亮。几把椅子摆在它周围,对着远处波光潋滟的湖面,一些杂志散落在一旁的桌子上。
那是一座美丽的小屋。
人的思维终究不只是推理,我们思索着时光,思索着生死,思索着我们曾路过的一切,像引力一样聚集着意义,试着给出最终的回答。
人工智能,也会需要这样一个小屋吗?
驾船穿过迷雾的辛顿,总有一天会和那个终极诘问重逢:如果人的生命布满苦难和离别,制造出更多像人一样的AI,意义是什么?
他也许仍然没有答案。
但至少,在苦难和苦难之间,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。
就像在冬天和冬天之间,有春天。
“人是机器。但人是特殊的、美妙的机器。”辛顿说。
辛顿的77岁,错愕地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明亮追光,迎来了全世界认识自己、倾听自己的渴望。他任人从身上摘下各种意义,像一颗秋天的树洒落金辉。
但那些意义,终究不是喜爱或无视他的人的自我投射吗?
辛顿只是如此生活了77年,冬天过去,春天到来,春天过去,冬天到来。
为了在残忍的时光里行进,他必须和苦痛作战,而为了和苦痛作战,他变得光辉闪耀。
他和你我一样是一台机器,也和你我一样,怀揣着谜一样的梦想。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,他的梦想一半走进了春天,一半埋葬在寒冬。
但那也许不重要。
因为所有凝聚起来的东西都会被时间的洪流再次冲散,一如横行的巨兽变成沉默的化石,一如奔涌的泪水消失在雨中。
重要的是,那些曾和他对望的人们,也许有一瞬间会轻轻慨叹:
“呐,是个温柔的人呀。”